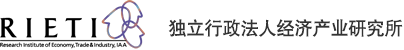立志成为经济学家
我于1957年出生于香港。战后的香港从一个收容难民的避难所一举发展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在大学毕业之前的22年里,我亲眼目睹了香港的高速增长时期,它也是亚洲奇迹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在"廉租屋"长大的孩子,对我来说,进入大学是日后出人头地必须通过的一道"关卡"。进入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我选择了热门的工商管理系,并在一年级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了经济学,尤其对凯恩斯学说产生了兴趣。
大学一年级结束时的1976年暑假,我第一次访问了中国大陆。那时候,呈现在眼前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支离破碎的中国经济,我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并几乎改变我的人生观。为什么作为一个由异民族统治的殖民地,并且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的香港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提出自力更生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经济却停滞了呢?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想答案也许就藏在经济学这一"经世济民"的学问中,于是在大学的第二年,我提出请求希望转入经济系,结果被批准了。当时在香港,经济系受人青睐的程度远远不如工商管理系,因此,很多经济系的学生转入了工商管理系,相反的情况几乎没有,难怪常有人对我说,"你真傻"。然而,抚今追昔,这就是我立志成为经济学家而迈出的第一步。
1976年,北京爆发了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接着毛主席逝世后,不久四人帮被逮捕。在此情况下,邓小平重新走入政坛,转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急剧变化。虽然香港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但学生们常常心系祖国,大家热心地阅读毛主席和马克思的著作。那时候,社会主义的实验已经花费了30年的时光岁月,然而中国不仅没有富裕起来,相反与日本和亚洲四小等国家和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看到这种状况,我已经不再对由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的现代化心存幻想。
对经济学的现状大失所望
相反,我把目光投入了亚洲唯一一个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并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为学习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经验,并争取赴日留学,我在选修课中选择了日本研究。当时,大学的老师建议我,要想成为经济学家,"就去美国吧"。然而,也得益于日本政府的奖学金,在大学毕业的同时,我于1979年10月进入东京大学留学。算上研修生和就读博士生课程的时间(当时5年一贯制),我在东京大学共呆了六年半,但现实与理想之间差距很大,使我大失所望。
在东京大学的研究生院研究科,上课时主要讲读论文,大家关心的主要是美国学术界的最新流行情况。经济学的学科编制也以理论为中心,实证分析不受重视。就连国际经济、劳动和金融等应用领域,也都几乎没有具体地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这一状况基本上如同经济学家Leijonhufvud笔下的寓言"Econ族的生态"所描绘的情形(注1)。也就是说,Econ族的阶级按照数理经济学、价格理论、国民收入分析、经济发展论、实证研究等专业领域的序列而决定,阶级内部的身分序列则由制作模型的能力来决定。东京大学的研究生们为了争取最高排序,都非常热衷于动用高等数学来制作模型。"但是,制作出来的大多数模型起不到实际作用,只是用作供奉神灵的供品(专业杂志上的陈列品)"。
按照Econ族的排序,我曾想学习的经济发展论和实证研究均被排在了最后。而且,让人遗憾的是虽身在日本,却无法系统地学习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对于那些变成了数字游戏和不切实际的理论,我又丝毫感觉不到其魅力所在,结果并未找到自己的研究课题,时间就速速流逝了。蓦然回首,将指导老师的代表作翻译成英文成了我就读研究生院期间唯一的学术成果。
作为智库研究员重新起步
在何时能获得博士学位仍然遥遥无期的情况下,1986年春天,我决定退学回到香港,但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没有拿到博士学位,所以无法找到大学的教职,做一个学者的路就这样也被完全封死了。最后,总算在汇丰银行经济研究部谋得一职,主要负责是调查发展中国家的国家风险,但工作内容与学术相去甚远。
幸运的是,得益于日本的泡沫景气和国际化的呼声,1987年夏天,作为一名经济研究员,我被日本最大的民间智库野村综合研究所聘用,再次返回了东京。当时的野综合研究所里到处充满了生气,与研究生院与世隔绝的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通过参加东京国际研究俱乐部等的研究活动,我有机会与海内外第一线的研究人员紧密地交流,同时与机构投资家和经营者的讨论也启发了我的思路。从此以后,我立志反败为胜,利用我靠近"市场"的优势,不断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深入研究日本与亚洲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发表了很多的著作和论文。特别是有关"日元圈"的一系列研究获得认可,并于1996年2月终于从东京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学位论文中,我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明确提出,在对美元稳定的汇率政策(钉住美元)下,日元与美元汇率的变动会带来亚洲各国经济的动荡,并建议采用提高日元比重的一篮子货币制度取代钉住美元政策。当时由于普遍认为钉住美元有助于亚洲的经济稳定,因此我的观点很难被人接受。但是,随后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暴使得钉住美元政策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一篮子货币的提议受到关注。作为委员,我应邀参加了日本大藏省外汇审议会,我所提议的有关亚洲各国汇率政策的建议被写进该会的报告书《面向21世纪的日元国际化——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与日本的对策》中。
以学位论文为基础撰写的《日元圈经济学》一书于1995年由日本经济新闻社出版,并于翌年获"亚洲太平洋奖"(该书英文版《Yen Bloc》,加入了对亚洲金融风暴中汇率因素的分析,2001年由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出版,其中文版也将面世)。以此作为分水岭,我开始致力研究70年代末步入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经济。在研究过程中,我感到在外汇政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开放"的一面,可以继续采用以往的研究方式,但是对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所表现的"改革"的一面,我感到必须采取新的研究方式,于是,我开始关注"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
与新制度经济学相遇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转入改革开放政策,放弃了由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做法,以引进市场机制为杠杆,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结果,今天的中国与我70年代中期首次访问时相比判若两国,呈现出惊人的变化。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工人那般懒散的作风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天中国人勤奋工作的精神令以勤勉著称的日本人也表示敬佩。这说明在思考经济发展的时候,制度是何等重要!
进入90年代之后,很多中国经济学家开始将科思(1991年诺贝尔奖得主)的交易费用理论、诺斯(1993年诺贝尔奖得主)的新经济史理论和布坎南(1986年诺贝尔奖得主)的公共选择理论等新制度学派的手法积极地应用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分析过程中。90年代中叶,汇集了这些方面的代表性论文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盛洪编,1994年)、《中国的奇迹》(林毅夫等,1994年)、《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樊纲,1996年)等书籍相继出版。这样,在中国的经济学界,新制度学派取代了传统的马克斯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主流派。该研究方法作为构筑"市场过渡经济学"的共通的范本日渐成型,"中国经济学派"也正在形成。
在领导这种市场转型经济学的学者中,大多数人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属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70年代后期进入大学的年轻一代。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农村,受过荒废青春的痛苦经历。他们之所以立志于经济学研究,是因为他们拥有明确的改变世界的意识。不仅留学欧美的"洋博士",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的"土博士"们也非常活跃。
关于在研究正在发生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所体会到的理性的愉悦,可称是中国新制度经济学大本营的天则研究所理事盛洪生动地说,"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制度变迁的时代,我们正亲眼看着猿变成人"(注2)。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通过政策建议和舆论形成,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着经济改革,他们非常自负,认为自己的使命不仅仅是发展经济学,而是发展中国经济本身。对他们而言,经济学不是象牙塔里的空泛理论,而是一门决定13亿人命运的经世济民的学问。
我与制度经济学的相遇可以追溯到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在80年代中叶以后发表的著作。张教授用通俗的中文撰写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一系列著书,如《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中国的经济革命》等被全球华人广为阅读,今天也在不断地给予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们以巨大的启发。进入90年代以后,我也接触到了大陆发表的相关文献,颇为感怀。近年来,通过各种各样的研究交流活动,与中国经济学派的人士交往日深。为了向日本的读者介绍一些中国经济学的最新潮流,1998年我监译了林毅夫先生的《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日文版《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一书(日本评论社),现正在计划将樊纲先生的著作翻译成日文出版。
在经济产业研究所潜心研究中国问题
2001年我转往经济产业研究所工作,从而获得了一个我梦寐以求的能够潜心从事中国研究的环境。特别是从青木昌彦所长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他确立了"比较制度分析"这一研究领域,并积极地将其运用于中国等转型期经济的研究。青木所长是日本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其著书已有七册被翻译成中文,研究成果在中国广为人知。
近年来中国经济崛起,其动向在日本也受到广泛关注。但是,在谈到中国的未来时,日本的舆论总是在"悲观论"和"乐观论"之间大幅摇摆,感情色彩非常明显,缺乏冷静的分析。为了让日本广大读者正确地理解中国经济的全貌,我于2001年7月在经济产业研究所的网站上开设了"中国经济新论"这一园地。在以中、英、日三种语文同时发表的专栏"实事求是"(这是象征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关键词之一)中,我围绕着中日关系发表时评,同时,积极地以日文介绍中国研究人员的分析和建议。其内容涉及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核心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学"、"中国的新经济"、"世界中的中国"、"中日关系"这五个领域。在当前中国热的推动下,这一园地自开设以来,读者点击次数与日俱增,其中不仅有专家和决策当局人士,更得到了广泛的读者支持。以"实事求是"栏目刊登的文章为中心汇编而成的《为日本人而写的中国经济再入门》,于2002年10月由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
我的故乡香港自1997年7月回归祖国,我也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人。另一方面,从进入东京大学的研究生院留学时算起,我在日本已居留20余年。我能够理解中日两国的语言和文化,我一直希望利用这一优势成为两国间的一座桥梁,然而,两国间的互不信任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我想采取"中立的"立场时,往往会受到两面夹击。在日本,我被说成"亲中派",在中国,我又被称为"亲日派"。在中日关系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化的今天,哪一种说法都不是褒奖之词。但是,21世纪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关键取决于中日关系,加深两国间的相互理解非常重要。我希望尽一点绵力,通过自己的研究活动作出贡献。若用诺贝尔奖来作比方,我企盼的也许并不是经济学奖,而是和平奖。
2003年2月10日
>> 日本语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