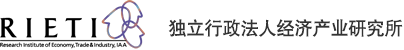在论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与家庭收支调查的储蓄率发生偏离的原因之前,本讲想首先弄清可进行比较的统计,并掌握其现状。
所谓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就是综合掌握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主的经济活动整体的统计,在进行宏观经济时不可或缺。在按制度部门划分的收支计算方面,分为家庭、企业和政府等掌握储蓄和投资的平衡。用家庭部门的储蓄除以可分配收入后得出的“家庭经济储蓄率”,是与家庭收支调查进行比较的项目。
另一方面,家庭收支调查是根据家庭收支账簿制作的微观统计,是了解按年龄层和收入水平等家庭属性划分的消费和储蓄行为,是用来根据微观经济学分析家庭收支决策的统计。与储蓄率相应的是,从可支配收入中减去消费支出后得出的“盈余”,再除以可支配收入得出的“盈余率”,在传统上,一直使用“两人以上家庭中的劳动者家庭(工薪家庭)”的统计结果。
观察1970年以来的储蓄率变化(参见图)可以看出,到1980年为止偏离幅度比较小,但是之后偏离幅度加大。而且一直到2000年左右,不仅在水平上,而且在变化的方向上也大不相同,最近依然存在着25%的显著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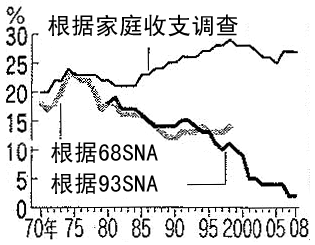
弄清这个偏离的原因,是对储蓄率下降进行分析的出发点。这两个数据是互补性的统计,通过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掌握宏观储蓄率的变化,并通过家庭收支调查,把宏观储蓄率变化分解为按家庭属性划分的储蓄率变化,就可以分析决定储蓄的机制。但是,如果存在偏离,就无法对微观与宏观进行一致的分析。
发生这种偏离,一部分是出于调查对象家庭和储蓄的定义等制度上的原因。但是正如先行研究中所指出的,即使对此进行调整,依然会有偏离残存。这些残存的偏离成为真正的“迷”,也是笔者在这里想要用“统计的倾向性”进行说明的部分。
以往的研究一方面关注制度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却一直放任了统计倾向性的问题。这是因为,要客观地找出存在倾向性问题本身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笔者将按照先行研究来调整制度上的差异,弄清统计倾向性问题的大小。
原载于2010年8月25日《日本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