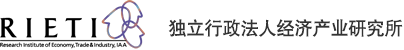当政府和执政党试图改变农业政策时,农民的收入必然成为问题。国家从来不会采取补贴非正式劳动者和倒闭关门的中小商店主等经济弱势群体,提高他们收入的政策,却只对农民,或平时为工薪人员,只在周末从事农业的兼职农民支付补贴,用国家税收保障他们的收入。在此次政府和执政党讨论改变减种政策的过程中,也讨论了农民的收入该怎么办,如何具体提高他们的收入。对于生活贫困户有支付生活救济费的制度,难道这还不够吗?为什么只有农民需要特殊对待呢?
根据农林水产省公布的试算,由于此次改变政策引进了新制度,对不种植用做主食的大米,改种饲料大米的农民,大幅度提高补贴金额,并向重新开展活动来维持农田的农民提供补贴,因此农业区域的平均农业收入将增加13%。当然,试算的前提是米价不下跌。
对于国会议员来说,由于政策的改变,选区的农民收入会发生什么变化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采取不利于农民的政策,下次选举时就有可能落选。
在最近的选举中,农业团体的农协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TPP(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运动,向农协承诺反对TPP和反对撤销农产品关税的候选人当选为国会议员。农业衰退,农民人口不断减少,为什么农民和农协的政治能量却不降反增呢?重要的原因是选举制度的改变。在只有两名候选人竞争的小选区制度下,如果有1%的选票流向对手,票数差就是2%,要挽回这个差距决非易事。有位众议院议员告诉我,“一到选举时,真的想‘杀死’对方候选人”。这恐怕不是胡言乱语。农民选票虽然已经没有让候选人当选的力量,但是在小选举区制度下,却拥有足以让候选人落选的力量。即便是1%的选票,也是不能丢失的团体票。在农村地区,农民选票占5%左右,对于候选人来说,没有比组织起来的压力团体票更可畏的了。
对于2010年民主党政权实施的农户分别补偿政策,自民党一直批评是乱发钱,在竞选纲领中承诺要废除,此次改变政策就是兑现竞选时的承诺。农户分别补偿制度是向完成减种目标数量的农户发放补偿,所以,媒体报道说废除农户分别补偿制度就是废除减种。其实改变减种本来并不是竞选议题。
所谓农户分别补偿就是对每10公亩稻田支付15000日元(这个估价的根据是对农户的保证价格与市场价格之差),另外,如果米价下降到一定水平以下时,支付该水平以下的部分。这个政策对本职为工薪人员的兼职农户也补偿农业收入,非常不合理,但受到农户的欢迎。顾名思义,这个政策是补偿农户的收入,因此废除这项政策,农户的收入就会减少,执政党的议员们担心选举时遇到困难。
结果,农户分别补偿没有立即废除,明年度保留7500日元半价。虽然按计划5年后全部废除,但正如2002年决定2007年停止大米生产目标数量(即减种目标)配额,但2007年刚一实施就立即撤销一样,在农业行政领域,很多时候,对将来的承诺都只是一纸空文。此次也一样,虽然自民党的选举纲领里承诺废除农户分别补偿,却没有兑现。而且没有一个农业相关人员追究违反竞选承诺的责任。
为什么只有农民的收入受到重视呢?因为只有农民收入成为政治问题
在中国,城市的收入是农村地区收入的3倍,这个问题成为内政上的最重要课题。实际上,二战前日本也曾经存在同样的问题,那时的农村比城市贫困。佃农必须把收获稻米的将近一半缴纳给地主作为地租,然后出售剩余的大米,用于购买第二年的肥料和生活费。因此,有的佃农甚至吃不到自己种的大米。据说还有人把大米放进竹筒里,在将死的人耳边摇竹筒,为死者送行。尤其是1930年的昭和大恐慌时,丰收导致米价暴跌,第二年东北和北海道却严重歉收,连自己的口粮也没有,东北出现了贩卖女儿的悲惨状况。
小仓武一和伊东正义等二战前进入农林水产省的官员,亲眼目睹农村的悲惨景象,感到了应改变农村贫困的责任。战前的农业官员们为了提高佃农的地位,不断地向代表地主阶级及其利益的帝国议会的议员们发起了挑战。他们的执着和热情结出的硕果就是战后的农田改革。在历史教科书里,记述了农田改革是GHQ(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和占领军实施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解散财阀等战后的经济改革中,只有农田改革是由日本政府农林水产省制定的方案。为了说服当时反对改革的保守党,借用了GHQ的力量。其实,制定并实施农田改革方案的是农林水产省。
通过农田改革,佃农成为小地主。农民把这些土地转卖给住宅和公共事业用地,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从大约1965年起,由于建设新产业城市等,农村附近形成了就业场所,使兼职农民增加。
由于机械化的进展,种植水稻所需的时间大幅度缩短,所以种植平均面积的稻田,只需周末作业就足够了。“米”字的写法是“八十八”,说种水稻需要88只手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电视剧里的“阿信”已经不存在。假设1天劳动8小时,1公顷面积的标准水稻农户1951年时全年需要劳动251天,2010年只需要劳动30天。因此,水稻农户的兼职经营显著增多。在农村经营农业的人基本上都是工薪人员,只在周末才去稻田做农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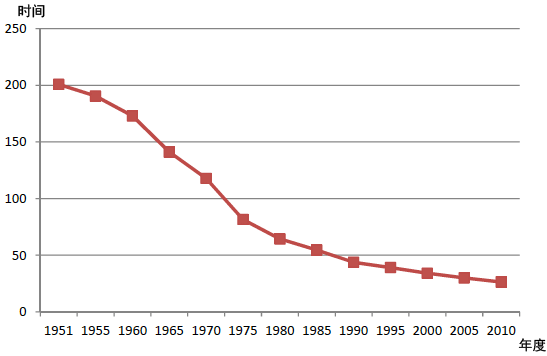
这些人虽然是小规模的农户,但因为他们又是工薪人员,所以并不是贫困户。1961年的农业基本法提出了改变工农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是从1965年以后,由于米价上涨和兼职经营的进展,农户的收入超过了工人家庭的收入,农村告别了贫困。在农户的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收入为110万日元,兼营等农业之外的收入高达432万日元,相当于农业收入的4倍,养老金等也有229万日元。现在的农村,虽然有小农,但没有贫农,小农是富裕的兼职农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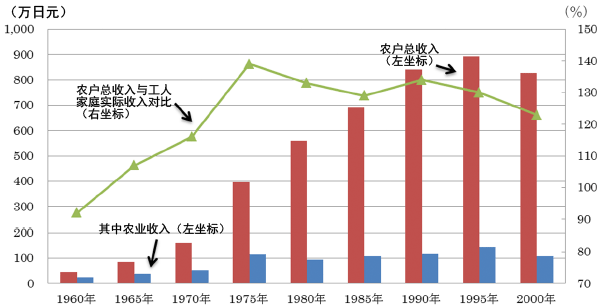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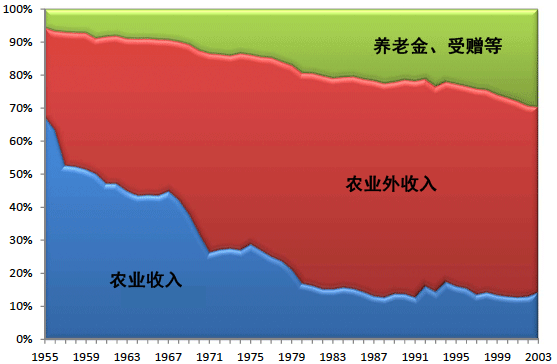
小规模兼职农户只能在周末从事农业,所以不能为农业投入许多时间。除草用农药,依靠多投入农药和化肥来节省时间和劳力。规模越大的农户投入农业的时间越多,对环境也越有利。水稻种植面积不满1公顷的农户,采取环保型农业措施的不到20%,而面积在10公顷以上的农户,采取措施的超过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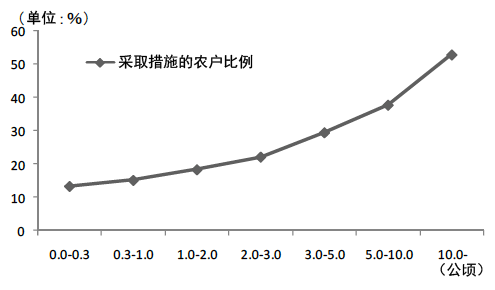
然而,许多国民居住在城市地区,长期远离农业,对农业和农村的知识和印象不是通过与农业和农村交往或实际体验,而是从学校教育、书本或者像《阿信》这样的电视剧得来的、被标准化的观念。也就是说,在农村,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贫穷的农民,千辛万苦地种植大米,这种印象已经形成了固定观念。贫苦农民连肥料和农药也不会使用,这种对战前的勤劳的小农印象引起了许多国民的怀旧之情,产生了对小规模兼职农户的共鸣,因此对富裕的农民产生了“保障他们的收入”的想法。
那么,是否不需要农业政策?
虽然不应担心农民收入问题,但是为了维持和加强向国民稳定提供食粮的粮食安全保障功能,以及养育水资源等,在农产品生产之外能够发挥的多方面功能,需要维持和发展农业。不过,这一切都是为了国民和消费者,二战前的农业官员不曾片刻忘记这一宗旨。农商务省第一位法学士柳田国男主张,不应提高米价以保障农民收入,应考虑消费者的利益,进口大米,降低米价。
战前曾两次出任农林大臣的农业官员代表石黑忠笃说过:“农业乃立国之本,应以为贵。不作为国本之农业不值一屑”。
但是,例如减种政策,为了维持高水平米价,一直采取减少在粮食安全保障上必不可少的农田资源,不把稻田用于发挥多方面功能的政策。这是为什么呢?粮食安全保障和多方面功能都是很好的概念,却从来没有从这些概念出发制定政策,只是在为了解释某项政策时,作为事后加上去的理由,使用了这些关键词。
现在的减种政策,减少大米生产,迫使国民消费者高价购买大米,是实施柳田国男以来的主流农业行政的人们深恶痛绝的做法。农业政策不应忘记“经世济民”这一经济政策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