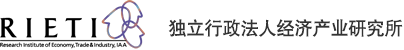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之前,显示OECD各国特殊合计出生率(TFR)与女性就业率(FLPR)关系的趋向和强度的相关系数为负值,经过80年代到90年代以后转变为正值。过去,女性就业率较低的国家出生率较高,现在,女性就业率高的国家,出生率变得较高。系数从80年代逐渐发生变化,以1986年为界由负值转变为正值。
因此,在欧洲各国和日本,人们提出了这样的理论,即“过去女性就业的增加导致了出生率降低的趋向,现在反而带来了出生率的提高,起到了阻止出生率下降倾向的作用”。但是这种观点的理论性依据尚不明确。这一理论是在变化的机制尚未明确的情况下,作为事实提出来的。对于已婚女性来说,从事正式职业与抚育幼儿二者难以兼顾,从这种普遍认识来考虑,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说明。
对此,2004年德国马普学会的研究员、经济人口学家Kogel及其共同研究者发表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两篇论文。他们假定OECD各国中存在尚未被观察到的对出生率产生影响的固定要素,运用排除该影响的“国别固定效果模式”的统计模式进行分析,其结果得出如下结论:
(1)在OECD各国,女性的FLPR与TFR的关系现在依然是负值,平均来看,女性就业的扩大与出生率下降有关。
(2)其呈现的负的关系,以前较为明显,1985年以后有所减弱。
也就是说,呈现正的关系不过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依然为负的关系,只不过负的关系有所减弱。但是,他们并没有说明这种变化是由什么引起的,而是作为新的研究课题留下来了。也就是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即“1980年以前,女性就业的增加造成出生率的减少,但是这种趋向逐渐减弱,其理由何在呢?”如果TFR与FLPR的关系现在也呈现负的相关关系,那么,解决低出生率问题与推进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就有可能从政策上互相矛盾,是极为不利的现象。因此,弄清两者呈现负的相关关系减弱的原因,切实反映到政策之中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下面,根据上述动机,笔者概述作为经济产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进行的研究结果(详见工作论文“关于女性就业和出生率的真实关系——OECD各国的分析”),讨论其结果对制定政策的意义。
■理论性假说
决定生育机会成本的主要有以下三个要素。第一是由教育和职业经验等个人的资质以及男女差别等社会性制约而决定的个人获取收入的能力,获取收入能力高则机会成本也高。第二个要素是由于生育而不得不离职或者变为计时工的程度,决定这一要素的主要是从女性的角度看待兼顾工作和家庭的难易程度。这种兼顾程度依存于
·家庭环境(丈夫是否分担家务及抚育幼儿等)
·职场环境(工作时间以及工作场所的灵活性等)
·地区环境(托儿所等设施是否充分等)
·法律环境(产假是否能得到保证,收入补偿是否充分等)
兼顾工作和家庭的程度高,则生育的机会成本就会降低。
第三个要素是由正式员工变为计时工而使工资大幅度减少、或者由于离职而难以恢复同种职业等,在劳动市场能否灵活就业的程度。决定这一要素的主要是雇用习惯的特性。伴随生育而离职或转职,再就业的机会和收入减少得越多,生育的机会成本就越高。
如果将决定生育机会成本的这些要素与前述Kogel的学说,即FLPR与TFR之间负的相关关系以20世纪80年代为过渡期,由以前较强的关系到90年代以后变为较弱的关系,结合起来,又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这一时期在OECD各国,女性获取收入的能力提高,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生育的机会成本应该上升,而实际上由于兼顾工作和家庭的程度以及可灵活工作的程度(合称为工作与家庭平衡,以下简称为“兼顾程度”)提高,机会成本减少的假说得以成立。这是由于如果其他条件相同的话,机会成本越低,女性的就业导致出生率降低的趋向就会减弱。因此,笔者将这一假说更为具体化,对下述两种机制的假说进行了实证研究。
〈假说1(交互作用效果假说)〉
女性就业率与出生率的负的相关关系依存于兼顾程度,如果兼顾程度增高,负的相关关系就会减弱(假说A)。现在兼顾程度比20世纪80年代以前高,所以负的相关关系有所减弱,(假说A')。
〈假说2(相抵性间接效果增大假说)〉
女性就业率对出生率的影响,除去直接性负的影响之外,还有以下的(1)和(2)相结合而产生的间接性正的影响。也就是说,(1)在就业率较高的OECD各国,随时代的变迁兼顾程度有所提高(假说B);(2)兼顾程度越高,出生率越高(假说B')。现在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兼顾程度高,所以,正的间接效果提高与负的直接效果部分相抵,负的相关关系有所减弱(假说B")。
其中,假说A'与假说B"是关于工作与家庭兼顾程度的OECD各国平均值有所提高的论点,由于无法得到各国关于兼顾程度的80年代以前的统计数据,所以不列在本次的分析对象之中。80年代之前还没有“关爱家庭的工作环境”、”工作与家庭兼顾”等概念,女性休产假的法律保证在许多国家也并不存在或者十分有限,所以当时兼顾程度低是必然的。对于其他的假说A、B、B',运用能够获得相关指数的OECD1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验证。另外,模仿Kogel等人的先行研究,在假定OECD各国存在影响出生率的尚未观察到的固定要素基础上,使用了国别固定效果模式。
分析结果
分析结果主要内容如下:
〈结果(1)〉
女性就业率较高,在OECD各国依然与平均出生率低相关联。
〈结果(2)〉
工作与家庭的兼顾程度高,出生率则有所提高。
〈结果(3)〉
女性就业率提高对生育的负面影响,随着工作与家庭兼顾程度的提高而减轻,如果兼顾程度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则负面影响为0。
〈结果(4)〉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女性就业率已经较高的OECD各国,工作与家庭兼顾程度现在较高,而另一方面,女性就业率在80年代以后提高的其他国家,工作与家庭兼顾程度现在依然较低。
这些发现表明,上述假说也通过数据得到验证。结果(1)与(3)验证了假说A,结果(2)验证了假说B',结果(4)验证了假说B。
然而,根据2001年的“OECD Employment Outlook”,兼顾程度指数实际上由更多的要素组成。因此,为了使分析更为周密,也将这些要素考虑在内,把兼顾程度分为“工作与生育的兼顾程度”和“职场与劳动市场灵活性带来的工作与家庭的兼顾程度”(以下称“由工作灵活性带来的兼顾程度”)两种。“工作与生育的兼顾程度”指的是招收不满5岁儿童的托儿设施的利用程度、以及休产假和收入保障方面的程度。而“由工作灵活性带来的兼顾程度”包括自由工作时间的普及程度、被作为优质计时工作就业形态的自发性计时工就业的普及程度等。经过分析,得出关于上述结果(2)、(3)、(4)的以下结论。
〈结果(2)的严密化〉
“工作与生育的兼顾程度”和“由工作灵活性带来的兼顾程度”都使出生率有所增加,而后者的影响更大一些。
〈结果(3)的严密化〉
女性就业率的提高给出生率带来的负面影响依存于“由工作灵活性带来的兼顾程度”,这种兼顾程度的增强时,影响就减弱,但是负面影响与“工作与生育的兼顾程度”无关。
〈结果(4)的严密化〉
20世纪80年代以前女性就业率已经很高,这与“工作与生育的兼顾程度”密切相关,而与“由工作灵活性带来的兼顾程度”关系不大。对结果(4)进行一些补充说明。托儿所的充实以及休产假等“工作与生育的兼顾程度”,80年代时主要在女性就业率较高的国家获得提高,但是职场和劳动市场灵活性带来的兼顾程度并不是随着女性就业率提高而提高的。这些结果中,交互作用效果假说(A、A')只有在“由工作灵活性带来的兼顾程度”的作用中才得以成立,而相抵性间接效果增大假说(B、B'、B")只有在“工作与生育的兼顾程度”上才成立。这个分析结果十分有趣,两种假说与两种兼顾程度的作用形成一对一的形式。
对制定政策的意义
首先应该指出,日本的工作和家庭的兼顾程度,在分析对象的18个国家中,仅次于排名最后的希腊,列倒数第二位,依然处于低水准。不过,用于评估的指标是反映90年代后期情况的数据,日本在其后通过改订休产假法以及实施新的天使计划等,努力提高了工作与生育的兼顾程度,因此,现在的情况比评估时有所好转,但是尚有许多要改善的地方。
笔者在最近的研究(“关于生育率低的决定性因素和对策:丈夫的作用、职场的作用、政府的作用、社会的作用”《家计经济研究》2005)中指出,能够休产假的职业女性的生育率与专职主妇基本相同,甚至有略高的趋势,而不能休产假的职业女性的生育率则大大低于专职主妇。
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离职后也较容易得到相同类型职业的雇用,所以休产假并不是那么重要的因素。但是在日本、南欧等一旦离职就很难返回相同类型职业的国家,能够休产假则显得特别重要。问题在于企业方面的合作,如果休产假对企业来说负担过重,就有可能在招聘职员时歧视女性,或者歧视准备休产假的女性等。为此,创造既不使企业感到负担增加,又能够使更多的人得到休产假机会的社会环境极为重要。关于这个问题的细节,请参考经济产业研究所政策分析论文(PAP)第6号“低出生率的决定性因素和具体对策——对已婚者的分析”,在此不加赘述。但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积极性,在引进基于休产假的实际情况发放补助金制度的同时,还可以考虑对优良企业进行奖励和宣传等方法。
另一方面,通过本次分析还发现,除去政府一直花大力气充实托儿所以及完善休产假制度(“工作与生育的兼顾程度”)以外,努力提高“由工作灵活性带来的兼顾程度”也十分重要。这种兼顾程度不仅要比“工作与生育兼顾程度”对出生率增加的贡献更大,而且还具有直接减弱女性就业增加造成出生率降低趋势的效果。2005年施行的支援养育下一代对策法,包括重新看待劳动方式的企业的作用,大方向是正确的。今后在明确具体政策的基础上,如扩大上班时间的自由、在家上班等时间和场所具有灵活性的职场、扩大高质量的计时工作范围、以及扩大离职者再就业机会等等。从充分活用女性人才的观点出发,我想指出以下几点:
首先,上班时间自由的工作体制,在以工作结果来评价工作的专门技术等职业中较为容易引进。但是,难以引进该项措施的其他职业该怎么办呢?作为一个提案,笔者认为可以进行制度改革,废除综合职务和一般职务的区别。这种差别间接地与歧视女性相关,妨碍从事一般职务女性充分发挥才能,造成工作缺乏灵活性的状态。作为替代,引进以往称为“职员”的“综合职务”和欧美式企业内职业资历型的“专业和职业资历职务”,使后者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具有灵活性,可以期待其有效发挥女性作用。
第二,所谓“高质量的计时工作”,是指除去工作时间少而带来的工资差别之外,在雇用的稳定和健康保险及养老保险等福利方面与正式职员享受同等待遇的计时工工作。在荷兰,企业可以根据员工的工作时间多少规定工资的差别,但以其他理由设置正式员工与计时工的区别,则视为违法。在正式职员拥有诸多附加福利的日本,虽然照搬荷兰的方式不大可能,但是应该改变正式员工与计时工之间的差别。
作为扩大再雇用的具体策略,对于以生育和护理病人为由的离职者,可以考虑采用与美国的“先任权”相似的制度。所谓先任权指的是企业根据工龄召回因企业一方的原因暂时辞退的员工的制度。日本的企业之所以不重新雇用接受过企业内训练的离职者,主要从重视忠诚于企业这种企业文化的角度对离职者加以惩罚,从充分利用人才方面看并没有合理性。在生育率低的老龄化社会,由于生育和护理老人而离职比忠诚于企业更具有正当性,当这些人希望复职时,其工龄、离职时间(比如五年以内)等如能满足一定条件,应优先考虑作为正式员工重新雇用,确立“生育、护理离职者先任权制度”。
职场和劳动市场灵活性的扩大有必要根据日本的现状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实现工作与家庭平衡,不仅仅是家庭的问题,同时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认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包括扩大对女性人才的利用,人们期待今后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