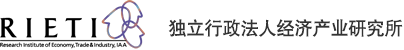序言
最近,搞活地区的讨论再次热烈起来。日本政府的"框架方针2014"明确写进了"50年后保持1亿人左右的稳定人口结构"。而且,为了地方创生和阻止人口减少,安倍政权还设立了"城镇、人员、工作创生本部"筹备室,以此应对日本特有的急速严重的低生育率老龄化和人口减少问题。
日本创生会议于几个月前公布的"可能消失"的地方行政区一览表,或许对中央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注1)。而且7月份在佐贺召开的全国地方行政长官会议上也进行了同样的讨论,通过了"低生育率非常事态宣言"。该宣言提出,应把低生育率对策纳入国家议事日程。
由总务省和国土交通省牵头,中央政府各机关也开始实施针对将来的对策。经济产业省也开始围绕"全球经济圈"和"地区经济圈"这两个经济圈,采取既能应对全球化经济,又能面向地区经济活性化的对策。各中央政府机关之间在政策上的共同思路是,一边在各地区之间分散功能,一边在各地区内部压缩功能,形成自力更生、高效率的经济活动。这种视点是在局部利用集群的同时,建立通过网络相互依存的经济结构,这正是空间经济学所擅长的领域。因此,本研究想从"空间"和"集群"的观点,思考各地区间的生育率为什么不同?今后应采取什么样的低生育率对策和增长战略(注2)?
什么地方生育率低?
我们从地区的视点,利用数据察看一下什么地方的总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较低(注3)。图1是各市区町村的总生育率地图,从大致倾向来看,呈西高东低的关系,九州、冲绳地区的总生育率平均高于北海道、东北地区。在各都道府县内部,越是城市地区总生育率越低。图2是各市区町村的人口密度地图,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为首的主要城市圈人口密度很高(注4)。图3显示出,从这两张地图可以推测,越是人口密度高的地区总生育率越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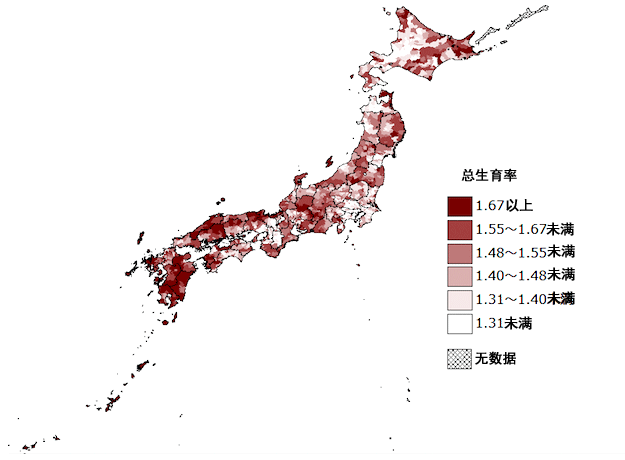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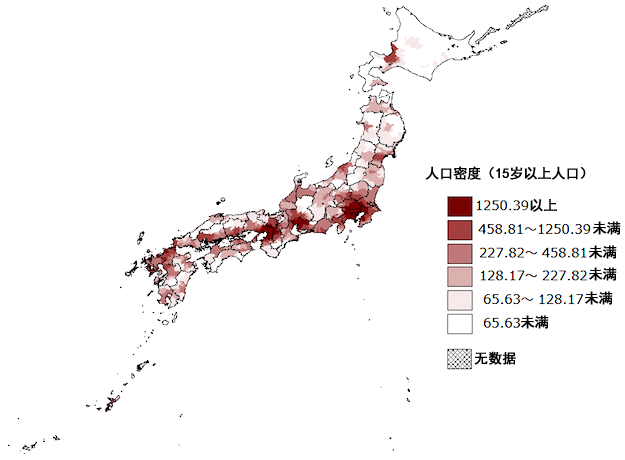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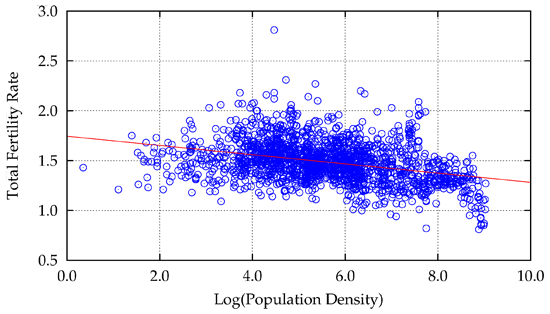
为什么人口密度高的地区生育率低呢?
以上是单纯的相关关系,强烈地显示出在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存在阻碍生育的因素。那么为什么人口密度高的地区生育率低呢?我们思考一下这种地区的因素。例如图4所示,文部科学省的《儿童学习调查》指出了人口规模越大校外活动费用越多的倾向。图5也显示,从总务省《全国物价统计调查》的全国物价地区差指数可以看出,越是城市,补习教育价格指数就越高。进而国家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生育动向基本调查》指出,与理想的孩子人数相比,实际上没有达到理想人数的主要理由是教育费用太高。因此可以推断,越是城市孩子的教育费用等越高,结果形成了孩子人数越少的倾向(注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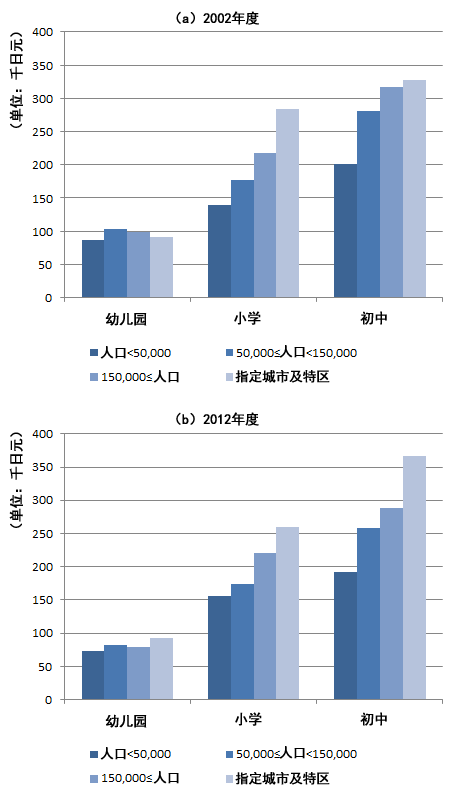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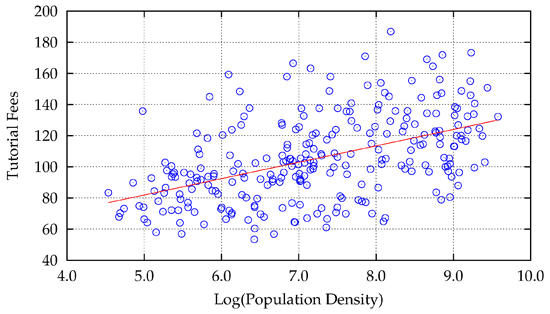
关于孩子的养育费上涨导致家庭孩子人数减少的价格效应,已有Becker(1960、1992)进行过分析(注6)。另外,从引进地区和集聚概念的Sato(2007)的分析加以类推,可以解释为,人口密度带来了孩子养育费的地理差异,这种差异又带来了地区间的生育率差异。进而还可以认为,为了养育孩子而辞去工作,越是在城市这种机会成本越高,这也是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注7)。Willis(1973)对这种机会成本导致低生育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如果只看这些问题,也许会觉得集聚带来的负面影响非常大,但是总的来看,从集聚得到的利益大于成本,其结果引起了人口向城市流动。
集聚果真导致生育率下降吗?
我们进一步深入讨论上述问题。集聚导致孩子养育费(包括机会成本)上涨的结果,在城市地区引起了低生育率,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呢?实际上,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还有很多,必须同时验证各种假说。例如可以考虑下述可能性。
越是居住在城市的人,越有可能结婚后仍然选择不要孩子。
越是生活在地方,养儿防老的作用越受重视,与城市比较,地方的生育率可能相对偏高。
越是居住在城市的人,越需要接受高等教育和就业,结果可能形成晚婚晚育,出现低生育率。
由于这些家庭的选择取向和性质的地理分布方式,可能看起来似乎是人口集聚带来了低生育率。应该注意的是,集聚本身并没有成为低生育率的直接原因。
由于家庭对居住地的内生性选择,人口集聚地的低生育率被夸大看待的情况不仅这些,例如还有下述可能性。
可能孩子越多的家庭越从城市迁居地方,而孩子少的家庭则留在了城市地区。
可能孩子越少的家庭越容易搬家,形成从地方移居城市的倾向。
这样,由于生育孩子之后的行为,有可能在集聚地进一步观察到低生育率。这时的集聚并没有直接抑制生育行为,而是对选择居住地产生了影响。因此,由于希望有孩子、或者已经有孩子的家庭搬出了集聚地,导致了夸大评价集聚抑制生育行为的直接效果(注8)。
笔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人口集聚本身与生育人数减少的因果关系是否真的存在,还是由于其他原因使城市看起来似乎出现了低生育率,对此还需要辨别。也就是说,正确了解原因,对于制定正确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确认结果是否经得起检验,如果集聚果真是导致低生育率的原因,就有必要测算影响的程度。为了制定有理有据政策,这是我们研究人员必须解决的紧迫课题(注9)。
集群经济政策也有可能导致生育率下降
低生育率老龄化、人口减少的社会受到劳动力无法增加的制约,因此,如何提高劳动力质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于搞活地区经济和实现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怎样才能提高生产率呢?现在备受关注的一个方法就是集群经济。经济产业研究所迄今也发行了许多相关的书籍和工作论文(注10),不过如前所述,集群经济的增长战略,应注意有可能进一步导致地区的低生育率。
在依靠集群经济实现增长战略的同时,需要实施对策,填补因此而发生的低生育率的影响。前面已经强调,在讨论应具体实施什么样的政策时,必须正确了解在集群地发生低生育率的原因。在这里笔者想举出两个事例,来探讨两种可能的原因及其对策。
第一个是地区间的养育费和生活费的差异带来的地区间的生育率差异。假设收入相同,那么养育费和生活费越高的地区,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量就越少。也就是说,在地区间即使名义收入相同,也会发生实际收入不相同的状况。因此,儿童补贴额不应全国一律,应根据儿童的年龄,同时考虑地区间养育费和生活费的差异来决定补贴额,这样或许可以减少生育行为所带来的差异。第二个是地区间的儿童等待入托的问题。不仅有托儿所不足的直接问题,还有越是人口集聚地区,寻找合适托儿所的费用就越高的问题。假设其结果导致生育率降低,那么就应更重视家庭能够及时利用托儿服务的政策(注11)。这种视点的特征是以地区为基础设计政策,在集群经济下不失为有效的手段。
当然还需要以家庭和企业为政策对象,推进工作生活平衡和支援育儿(注12),尤其是实施低生育率对策应尊重多种多样的生活周期。城市和地方的一大差异是生育的时机,图6表示各都道府县之间的生育时机差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居住在东京圈的家庭生活周期,生育的时机为35岁—44岁,年龄高于地方。也就是说,早生孩子还是晚生孩子的生育时机与城市规模相关。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地方建设城市时,不能排除晚婚晚育的可能性。为此,尊重各种家庭的生活周期,建立支援体制,使夫妻最终生育子女数能够接近理想的子女人数,就变得非常重要(注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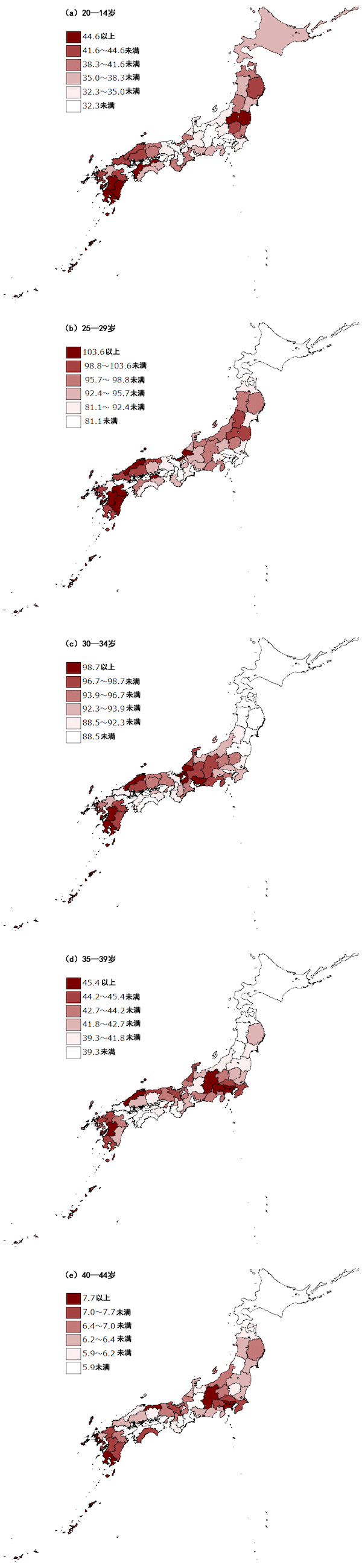
如何兼顾今后的增长战略与低生育率对策
本文讨论了如果没有低生育率的补充对策时,集群经济的增长战略可能进一步降低地区生育率。在促进搞活地区和经济增长的同时,如何尊重家庭多种多样的生活周期,阻止低生育率,是制定政策的重要视点。轻率地讨论向地方转移人口,可能在人口减少社会引起各地方行政区之间争夺人口的不毛之战,应避免一个地区依靠夺取其他地区的财富来实现繁荣的政策。
最后,笔者想就最近成为话题的市区町村"可能消失"的问题阐述一下见解。必须引起注意的是,各地区的家庭和企业并不是为了维持地方行政区的存续而存在的。现在到了应思考地方行政区应有方式的时期,把支撑地方经济的家庭和企业作为政策对象,并设计正确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视点。
鸣谢
在执笔本论文的过程中,得到了森川正之副所长的保贵意见,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其余有误之处都是笔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