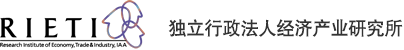编辑部:
您最近出版了《美国的贸易政治》一书的第四版。美国的贸易政策或国际贸易环境中的哪些新问题促使您写出新的版本?
Destler:
出版第四版的原因之一当然是因为该书第三版发行以后的10年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在国际方面,WTO(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一个举世瞩目的机构已经出现,长期以来一直执行的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已被逐步废除,新一轮全球贸易谈判——多哈回合已启动。在美国的政策中,自由贸易协议已成为更高的优先权(在东亚似乎也是如此)。
然而,正如书名所表明的那样,我的基本焦点是美国的贸易政治。我已将书中的修改部分集中在三个主要发展方面。我相信这三个方面使贸易政治与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撰写第一版时大为不同。
第一,正如在第九章中详细说明的那样,在美国,传统的、以商业为基础的保护主义比美国建国以来的要薄弱;第二,在贸易政治日程中,社会问题已上升到明显的位置,尤其是贸易与劳动力和环境标准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全球化的广泛分布影响之间的关系;第三,党派间的怨恨已开始统治美国的政治,特别是在国会中非常严重,在众议院中尤甚。
在第一版到第三版中,《美国的贸易政治》一书的核心议题是寻求保护主义的集中型利益和从贸易扩张中获利的分散型利益之间的政治不平衡性。其中心是国内的生产者,他们的产品与进口产品竞争。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寻求保护的产业的数量在萎缩,尽管美国的贸易逆差已达到创纪录的水平。我认为,其原因是大多数的美国企业已走向全球,生产者依靠国外的进口产品。他们的贸易政治的战略设想是国际商业将继续扩大。即使是在美国长期起主导保护主义作用的纺织业已从重点放在限制进口转移到使进口的服装最大程度地使用美国产的纤维和面料。
在数十年中,鼓吹自由贸易的人已使恢复到"斯穆特-霍利"水平的关税的幽灵复活,保护主义肆虐。这似乎不再是真正的危险。但仍然存在针对贸易进一步自由化的政治壁垒。
这些新政治挑战中显而易见的是社会问题的增多。自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谈判以来,美国贸易政治的绝大部分已集中在贸易与其他主要政策问题之间的关系上。由于受使生产者较少受到保护主义影响的全球化的驱动,"贸易与......"问题(贸易与劳动力标准,贸易与环境,等等)所涉及的不是在经济利益和目标之间保持平衡的问题,而是在经济问题和其他社会价值之间保持适当平衡的问题。美国的贸易政策机构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应对这一挑战,甚至没有做好理解它的充分准备。社会问题已削弱了两党的共识,而以往的贸易自由化法令正是以此为基础的。这些社会问题的影响在比尔·克林顿总统没有能够从国会中赢得快速谈判授权,以及导致1999年西雅图WTO部长级会议失败的游行中突出表现出来。
最后一点是美国的政治集团中,特别是美国国会中,几十年以来的党派分级化在过去几年中达到了高峰。这是由贸易政策之外的广泛力量所驱动的。但这种分极化已削弱了支持贸易自由化的久经考验的源泉之一:在委员会和商会一级领导人中的两党合作。
有关贸易问题的两党之争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得到加强。但2000年以后,它达到了近7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中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2001年提出了各自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的议案。尽管重大分歧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它们的领导人从未举行过严肃、认真的会谈来协调这些分歧。结果,乔治·布什总统不得不依靠前所未有的共和党人的支持,以维持一票之差取胜的优势。这迫使政府以非常微弱的政治优势谈判,降低了政府在特殊利益中起主导作用的威力。美国的食糖生产者发起了一场严肃的运动挫败了与中美洲及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美洲-多米尼加自由贸易协定),尽管该协定给予这些国家非常少的进入美国市场的新途径。
因此,尽管保护主义的削弱意味着全球化已在美国出现,但对美国来说,目前实行主要的新贸易自由化是非常困难的。这威胁到多哈回合的成功,因为在维护受保护的产业(包括食糖业)方面美国为达到有效的结果,必需做出重要的让步。
这就提出了美国应该怎样做的问题。新版的《美国的贸易政治》通过引用对从开放型贸易中所获得的巨大国家收益得出新的分析结论——在每年增加的国民收入中大约为1万亿美元。同样的分析还断定取消现存的贸易壁垒可加强美国的收入,年额外收入为5000亿美元。但是,这些收益并未平均分配,少数人会从贸易竞争中蒙受严重的工作和收入损失。这削弱了人们对新贸易谈判的支持。从政治上讲,这一点和上面所强调的社会问题及党派分极化的问题一起,使从贸易中实现这些潜在的收益非常困难。
解决这些重大政治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将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同更为慷慨、有效的国内政策结合起来,以补偿因经济变化而受到损害的美国人,使他们能更有效地参与到全球经济中去。这要求将重新培训、薪水、工资保险及其他措施结合在一起,费用约为每年200亿美元。当前的政治环境不利于这项计划。但是对从贸易中获利感兴趣的美国领导人很快就会发现这种逻辑不可抗拒。
编辑部:
在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对于美国的决策者来说,美国与日本的贸易逆差被视为主要问题。现在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似乎更为严重。这两种关系有何不同?
Destler:
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作为我们最主要、最有争议的关系取代了美日关系。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就绝对意义和构成成份而言正在扩大,超过了与日本以往任何时候的逆差。这两种逆差在反映全球贸易不平衡方面——美国的巨额往来帐户逆差、美国贸易伙伴的巨额顺差——是类似的。这两种逆差还反映出一种奇特的相互依赖的变体——美国依靠中国(而且仍然极大地依靠日本)为其逆差融资;中国(而且日本也极大地)需要美国为其产品提供需求,为其工人提供工作机会。
然而,不同之处超过了相同之处。就直接的经济方面而言,中国的贸易在这十年中的成功对美国生产者的直接威胁小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成功对美国的直接威胁。原因是中国是一个欠发达经济体制国家,它所装运的越过太平洋的产品不太可能威胁到美国的重要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在美国不断增长的市场份额是以其他外国竞争者为代价的。因此,美国产业对此的反应并不非常强烈,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我们与中国没有类似于美日之间半导体和汽车摩擦那样的问题。
然而,在其他方面,美中贸易摩擦更具威胁性。日本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美国在安全方面的同盟,在军事问题上会响应美国的带头作用。中国则不然(而且随着苏联的消亡,美国和中国不再有一个共同的超级大国对手)。日本是一个民主制国家,美国即使没有必要理解其广泛的政治进程的话,也能认可。中国目前是一个强权国家,人们仍在猜测其前景。一个相关的事实是日本已将有效的经济增长政策同在能产生大量政治热点的贸易问题上准备迎合美国相结合。东京的倾向已经是适应美国的政治压力。中国用不同的方法看待自已的历史。她对压力的典型性反应是作出强硬的姿态。这使得改善造成紧张关系的重要源泉变得更为困难——像在中国将人民币贬值及纺织品出口中的后多边纤维协议的热潮。
最后一点是中国的人口和经济增长以及潜在的能力使其成为极有可能在未来某个阶段与美国全面挑战显要地位的国家。这很自然使中国成为发生最严峻情况时的国防事务和经济方案的焦点,并使美国保持贸易顺差的努力复杂化。
编辑部:
在您的许多著作中,谈到在美国贸易政策中增加党派力量的重要性,为什么会是这样?需要做哪些事情来恢复对美国更为自由的贸易的广泛共识?
Destler:
总体而言,在美国人当中,党派力量的增长是温和的,但在两个政党的积极分子中已非常显著。引用莫里斯·菲奥里纳的一部杰作《文化战争?美国两极化之谜》中的话就是,在某些方面,这些积极分子已"劫持"政治进程。这种不断增长的党派力量有许多原因。其中最致命的是划分国会议员区域,使一个党派或另一个党派中的绝大数人安全。这意味着国会议员面临的政治压力不是来自政治领域中的另一方,而是来自己阵营的极端主义者。这些人会对被认为是过于温和的现任议员发出挑战。
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恢复些许的两党共识并非易事。如果所有的州都像爱俄华州那样通过独立的、非党派的机构划分国会议员区域的话,那将有所帮助。这将产生离政治中心更近的立法者。阿莫德·施瓦辛格州长已提议加利福尼亚州这样做。但是在贸易政策领域,争取恢复两党共识的最佳办法是将贸易扩张同我早先谈到的-并在《美国的贸易政治》一书中更为详细解释的-那类补救计划相结合。
- RIETI政策研讨会 面向打开新一轮WTO谈判僵局——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课题和日本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