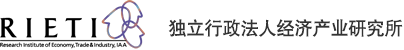RIETI客座研究员罗纳德·多尔50年来一直致力于有关日本的研究,其日文著作无论是数量还是内容都很丰富,被称作“日本研究的第一人”。特别是他于2001年出版的《股票资本主义 : 福利资本主义》(原题:Stock Market Capitalism : Welfare Capitalism)在日本荣登年度排行榜,并获得了第42届经济学家特别奖。近日,中文网站编辑部就福利资本主义与股票资本主义的差异、日本近十年来的变化、旁观者眼中的中日关系等大家关心的话题采访了多尔先生。
- 编辑部:
您被称作“英国最具代表性的日本研究家”,“日本研究的第一人”,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从事日本研究的经过以及研究的主要内容吗?
- 多尔先生:
我最初学习日语是为了在战争时期和日本作战。升入高中的时候,我的第一志愿本来是土耳其语陆军情报部翻译,但被指定为日语,当时还有点不情愿,后来才发现是如此幸运。
我最早来日本是在1950年。虽然在那之前我早就拿到了留学奖学金,可是占领军迟迟不给研究者签证。之后我终于得到了在日本居留一年半的机会,我希望在此期间能尽可能去理解日本这个与养育我的英国在很多方面都截然不同的国度。作为博士论文的课题,在英国我学习了江户时代的教育制度和儒教,但当我来到日本,我就把这种以图书馆为中心的理论学习暂放一边,全心投入到了社会调查中。我在上野附近的街巷中做的调查后来成为了《都市中的日本人》这本书的素材。这之后的1955年,我又一次来到日本,做关于农村的调查,并写了《日本农村的土地改革》这本书。从60年代起,我主要集中对劳资关系、雇用关系、企业治理以及宏观经济动向等国家经济制度方面进行研究。
- 编辑部:
您的日文著作无论是数量还是内容都很丰富,尤其是2001年出版的《股票资本主义 : 福利资本主义》(原题:Stock Market Capitalism : Welfare Capitalism)不仅在日本荣登年度排行榜,并获得了第42届经济学家特别奖。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也推出了它的中文版。在您看来,股票资本主义与福利资本主义有何差异呢?
- 多尔先生:
我在谈到日本经济体系时,一般会与英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盎格鲁·撒克森国家进行对比。我们将其简称为“AS模式”吧!与“劳动雇佣资本”相对,资本主义是“资本雇用劳动”的制度。如果这样进行界定的话,AS模式就可称为彻底的资本主义了。因为它不仅能够通过恶意收购,将整个企业纳为己有,也可以为了使资本的所有者—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而在适当的时候炒人鱿鱼。但是,传统的日本模式更接近于前者——劳动雇用资本。在相互持股的情况下,稳定的股东加大了收购企业的难度,要解雇“公司职员”也非常棘手,就算是要牺牲那些大股东的利益,公司也不会裁员。也就是说,日本的“公司”在很多方面类似中国的“单位”。如果从最抽象的角度对上述两种类型进行比较的话,概括起来有以下两点:
1、投机的角度。在AS模式中,就金融方面而言,投机因素浓厚的股票市场是资金供给的主要渠道;而在日本模式中,主要的资金筹措方式是存款人依一定存款利率存入款项,然后银行再按一定的贷款利率向企业提供资金。
2、作为个人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个人选择自由的重要性。AS模式国家中,每个人无论在哪里、干什么、投资什么公司、从谁手里订购零部件、使用哪家银行的服务,都可以潇洒地对过往的一切道声再见,第二天再与全新的对象发生往来关系,他们非常重视个人选择的自由。在日本,人们则尽可能地生活在“信任关系网”中,尽量建立长期性的往来关系。大型企业的雇佣制度原则上也是终身制。所谓的主银行制度,以及与承包订购企业所建立的长期交易关系,都是同一症候群的不同表现形式。为了维持长期的往来关系,人们不仅要考虑自身利益,还要多少顾及对方的利益。因此,对他人的“同情”就变得重要起来。此外,与AS模式国家相比,目前日本的收入分配比以前更为平均,这与上述原因不无干系。也就是说,日本的贫富差距并没有拉得太大。
- 编辑部:
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发展停滞,有人说是“失去的10年”,也有人认为,这10年里日本社会发生了诸多变化,是进步的10年。您是怎么看的?
- 多尔先生:
事实上,日本社会存在着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老龄化问题、少子化问题、以及由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人口向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人口转化致使经济高速成长过程终结,引起社会对低经济增长率的适应性问题。但是,日本这10年间发生的种种变化,并不是源于解决上述问题,而是有着其他方面的原因。毫无疑问,通货膨胀下的泡沫经济崩溃对日本经济影响深远。大家刚以为总算要从这种打击中站起来的时候,就遭受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金融机构纷纷破产,而日本政府则过早实施了金融紧缩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陷入了全面的通货紧缩状态,即使有了一些经济复苏的迹象,但仍无法从通货紧缩的泥潭中挣扎出来。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产生的危机感所催生出来的,是与实质性的结构问题、经济萧条的周期性循环问题都没什么关系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运动。即,政府为了使日本经济在制度上成为一种类似美国的经济,而实施了一系列放宽管制、劳动市场弹性化、市场主义的民尊官卑的政策。
改革的其中一环就是推行“企业不属于职工,而属于股东”的思想。与此同时,1990年时只持有日本企业6%股份的外商,现在则占据了日本市场的20%,他们从“沉默”的股东一下子变得声高气盛。企业经营者则今非昔比,必须时时留意着股价进行经营。公司的声望会随着股价的涨跌起起落落,而一旦股价下跌就会成为恶意收购的对象。——多数人认为,这种AS模式资本主义的惯用做法移师日本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 编辑部
据您观察,在这种倾向下,日式经营的三件法宝(终身雇用、按资论酬、企业内工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 多尔先生:
要说上述倾向引起了日本企业的形态或是日式经营的三件法宝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目前阶段尚不明显。尽管因国内需求减少,一些濒临破产的企业进行了重组,但采取的方式并非是解雇员工,而是有相当多补偿的劝退。修改劳动基准法时,有人曾提出废除支持终身雇用制的案例法,强化企业经营者的解雇权,可多数人对此表示反对,认为“为时尚早”,因此这种提议没有得以实现。也许,待将来上述倾向越来越强烈时,大家可能就会认为“时机到了”。话虽如此,人们心目中的优秀企业——佳能、丰田的社长们却认为“终身雇用体制是日本的优势”,一直采取着捍卫传统的态度。
至于企业工会,它给人的感觉是,在股东声音增大的同时,公司内部工会的声音却在变小。由于公司收益止步不前,再加上通货紧缩,因此即使名义上工资不提高,但实际上工资却在上涨。在这样的时代,工会在每年春季的运动中要求提高工资的理由变得不再充分,很多公司已废除了与工资相关的集体谈判制度,将工资结构纳入了劳动合同制。
企业内部变化最大的,是工资、薪酬制定中的“工作年限因素”在变小,很多公司改为按业绩计酬。但也有的公司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设定业绩标准、公平评价业绩的难度较大,公司内部由此引发的种种摩擦反而导致生产率下降。将来到底会如何发展,目前还难以预料。
但是,工会里确实也有一种呼声是愈来愈强烈的,他们提出“按工作年限论酬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应按业绩计酬。”这与政治领域中的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倾向不谋而合。从围绕养老金问题的政治动向也可以看出,国家为了使贫富差距不致过大而采取的,将全体国民的生活作为市民权加以保障的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制度,就是这种“不公平”的表现形式。在“自我责任”的口号下,按“业绩”分配引起再大的贫富差距也属正常。但目前处于统治地位的,是主张建立社会保障安全网的思想,即,应根据个人资产调查的结果向弱者提供最基本的补贴。
- 编辑部:
您认为目前中国所走的道路与几十年前的日本相似吗?
- 多尔先生:
在某些方面是这样的。经济中农业比重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不断扩大,这些所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是大体相同的。另外,战后日本的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45%,而中国尚占70%,因此中国的这种高速增长期可能会比日本还要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相似点,就是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时,大学教育、特别是理科教育急剧发展,形成了当今日本技术力量的基础。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过程,但二者的起点不同,中国人可以向着比60年代的日本人所学的技术更为先进的,IT革命之后的技术飞跃。
另外还有一点,同样可称为是“时代差异”。这就是最近不断变化的日本的AS模式资本主义,正在对处于工业化发展初期阶段的中国施加着影响。中国的国营企业曾经有过向日本模式的职工主权型企业发展的显著苗头,但是从过去5、6年来民营化、“单位思想”衰退、政府奖励市场个人主义等一系列动向来看,倒是向AS模式企业发展的可能性更大。
- 编辑部:
您是否能为发展中的中国提个忠告?
- 多尔先生:
希望不要过于轻信那些在美国研究生院获得了博士头衔的、认为美国经济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先进”经济并在任何方面都是典范的经济学者们的话。
- 编辑部:
最后一个提问可能稍微偏离了您的研究领域。您知道,中日关系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经济热,政治冷”。您从旁观者的角度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对于如何探讨未来的中日关系,您有何见教?
- 多尔先生:
- 对于中日关系的复杂化,我感到非常遗憾。有相当的事实令人对中日关系的未来担忧。这是因为,美国并不会自动让出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霸权;同时,中国对美国间谍飞机自由出入中国海岸的现象也不会永远容忍下去。中国的理科人才资源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丰富起来,这种丰富资源里的相当一部分是被派去从事电子武器的开发工作吧——开发可以防御美国导弹的导弹。美国宣称“决不允许出现在军事上能够抗衡美国的国家”,中国则想要处于与美国对等的地位,二者之间很有可能会陷入冷战状态。到那时,越是参与导弹防御系统的共同开发,就越是要与美国牵扯在一起的日本就会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与欧美国家个人主义的传统思想不同,中日两国都有着儒教的传统思想,不知到那时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是否还有人能回想起这一点。不管怎样,我认为,在探讨构建什么样的中日关系时,不仅应考虑到两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还必须意识到未来的军事环境是有可能向着上述方向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