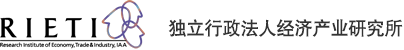据今年5月7日BOOKasahi.com报道,岩井克人先生在采访中就“安倍经济学”相关问题做了如下阐述。
“预期”可以成为社会动力
“所谓资本主义,就是有钱但没有智慧的人借钱给有智慧但没有钱的人,使智慧转化为现实的体制。当通货紧缩时,只要有钱就有利,人们对钱本身投机,因而发生惜贷。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使人们从对钱本身投机转向对智慧投机,进而对物品投资。”
“在这个意义上,‘预期’不仅使钱生钱,而且对经济本身产生巨大影响。围绕经济政策,有人说‘只靠预期,实体经济并没有跟上’,但是对于伴随货币的经济来说,甚至可以说预期就是本质”。
岩井先生的发言富于重要的启示,他所描绘的资本主义在硅谷的IT产业是日常现实。另一方面,当置身芝加哥时,就会经常听到从微观经济构想到宏观经济社会问题的阐述。在谈论“预期”时,卢卡斯学派的合理预期论认为,预期的形成可以促使政策干预消失。不过,岩井先生指出的问题点是,在不确定的宏观经济状况下,对货币价值的预期可以提高特定投机行为的激励机制,成为社会变化的原因。当预期的形成不仅停留在个人获得客观信息的结果,而且具有社会传播性质时,就会变成社会变化的动力。
人们的这种预期形成带来的影响不仅限于对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的预期产生的影响。笔者日前受邀在政府关于低生育率对策的专家委员会做了报告,就实现工作生活平衡社会的重要性,根据分析结果阐述了笔者的一贯主张。这个委员会是非公开组织,在这里隐去名称。一位委员“工作生活平衡对于低生育率对策并不重要”的发言令笔者震惊。据那位委员说,日本低生育率的原因“有近8成是由于晚婚化和不婚化”,其余的是由于婚后的生育率下降。假设后者中有半数是因缺乏工作生活平衡造成的,“其影响也只有10%左右”。听了这个意见,笔者当时感到“这种说法不对”,后来经过核实再次感到“确实不对”。首先,“不对”是因为那位委员虽然没有明说,但他认定工作生活平衡状况的影响发生在婚后。一般来说,晚婚化是低生育率的所谓内生变数(低生育率很可能同时引发了晚婚化现象),很难说是出于单独的原因。笔者确信,晚婚化和不婚化不能说与工作生活平衡无关。其他委员也有人对他的发言做了重要指正:“一旦结婚,工作和生育子女很难兼顾,因此有的女性对结婚犹豫不决”。但是由于笔者当时无法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实证性反证,因此在这种场合,作为学者的常规,没有进行强烈的反驳。对此,本文兼具补充说明的意思。
晚婚化、不婚化与婚后工作和生育子女兼顾度低相关
在这里重要的是,正如岩井先生所说,预期的形成会产生影响。笔者以前曾经以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对象,分析了女性参加劳动率的变化与出生率变化之间的关系。笔者察看了当时使用的特殊总计初婚率(Total First Marriage Rate)的经时变化与在该分析中使用的工作生活平衡指标(综合指标及其两大因素“工作与生育子女兼顾程度”和“工作方式的灵活性带来的兼顾程度”)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果如下表所示,从截矩来看,平均初婚率不断下降(晚婚化、不婚化不断进展),在工作生活平衡的实现程度、特别是产假及产假收入填补率、保育园或托儿所的充实程度等“工作与生育子女的兼顾程度”较高的国家,晚婚化、不婚化也显示出非偶然地较低倾向。在变化率的分析方面,排除了各国观察不到的异质性带来的影响,但还需要在排除可能产生外表关系的其他变化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更加严谨的分析。不过,在“工作与生育子女兼顾程度”高的OECD各国中,按照高低顺序,丹麦、瑞典、芬兰三个北欧国家排在最前面,在1980—2002年的大约20年期间,许多国家都经历了晚婚化,唯独丹麦例外,在这一期间初婚率反而增加,也就是出现了早婚化,瑞典和芬兰的晚婚化和不婚化倾向也比较小。这很可能不单是外表关系。如果“工作与生育子女兼顾程度”可以减缓晚婚化的进展,那么,无视女性对于结婚后会出现什么情况的预期形成所带来的影响,就无法考察因果关系。在日本,6成以上的女性因生育子女而退职,未婚女性对此耳闻目睹,就会想像婚后的生活。晚婚化与工作生活平衡无关的前提会导致错误的政策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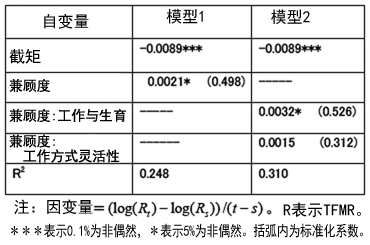
需要使被雇用者形成新预期的政策愿景
笔者对日本的男女共同参与的落后状况也反复指出,企业的“女性早晚要辞职”的偏见,通过在统计上对女性的歧视,导致了女性高辞职率的结果,这就是自我实现预言。这种预期不同于上述工作生活平衡与晚婚化的关系,“预期”不是女性对于自己的将来,而是企业这一外部因素强加的,却导致了“预期成真”的实际状态。
现在在日本,作为就业制度改革的一环,放宽企业整顿解雇员工的条件提上了议事日程。作为一般论,笔者赞同促进就业的流动化,但是如果说理想的社会本应是无论什么雇用形态,都可以获得平等的机会,尽可能活用更多的人才,那么当笔者听说将把原有的正式员工分为不限定于特定职务的传统型和限定于特定职务的JOB型,或者设置“限定员工”等方式时,总感到缺失了什么重要的视点。这视点不是“预见失业率增加,充实社会保障网”这类虽然重要,但已经说过很多的问题。缺失的视点是愿景,即制度改革能够给多种多样的被雇用者带来什么样的预期,以及预期形成的结果会怎样改变社会。不能成为企业进行人才投资的主要对象的被雇用者,其劳动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他们自己对自身投资的愿望,而这种愿望取决于能否形成预期,对自身的投资(自觉掌握新知识和技术,为加强资历而努力提高现有工作的质量)即便存在不确定性,也可以预期将来获得回报。如果日本企业今后仍旧把传统型的长期雇用、长时间劳动的正式员工作为核心,使其他被雇用者边缘化,那就只是在就业领域重新制定了一种身份制度,剥夺了被边缘化的多种多样的被雇用者对未来的希望。笔者认为,就业制度改革首先应从如何改变日本社会的观点重新思考,即使不是传统的正式员工,也能形成各种劳动形式的被雇用者对“努力和自我投资必有回报”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