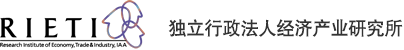政府的行政透明度、政府的职能以及公共能力问题
秦 海(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政策规划组副组长、《比较》编委)
非常感谢青木教授刚才的报告,我们这么多年都是读青木教授的比较经济体制的书和文章的,然后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同时也读毅夫教授的农业技术变迁、中国奇迹和国有企业自身能力来看中国改革的鼓点怎么走。在这里,由于职业的问题,经济问题我就不讲了,关于政府职能的调整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这个现在已经成为上下的一种共识,所以借此机会,作为对青木教授刚才两次的回应,就政府的行政透明度、政府的职能以及公共能力问题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我想,不管是模块化时代也好还是现在讲信息技术在政府中的应用也好,引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使得从80年代初期被称为索罗悖论的东西现在正在得到改进。比如说所谓信息通讯技术可能到处都存在,但是对生产率的变化我们看不到,但是这种东西在90年代后期有一些改进,特别是美国像Jensen、Gordon他们在研究中得到了一些证据,中国也得到了一些证据,这是在经济活动的层面。在政府活动的层面也引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就是E-government的兴起,是电子政府的兴起。我想,电子政府的兴起除了同IT革命有关,也同参与政府活动或者说要求政府提供什么样服务的整个博弈者范围发生很大的变化有关系。所以我想,斯坦福大学有两个非常著名的研究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的教授,一个是Paul David,一个是Avner Grief,Paul David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他说历史是制度变迁的载体,这一点非常重要,Path Dependence这个概念是从他8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来的。那么,关于制度作为一种规则来看,同时在特定的范围也和特定的界限上来看待的时候,Grief提出非常重要的东西,也是被青木教授在他的比较制度分析一书中引用的,这就是所谓common belief,也即所谓共享的信念。我们可能把它看成一个参与经济活动的所有人可能演化出来的共同的信念。
第二个是作为博弈者的预期对制度变化非常重要,那么这种东西如果跟IT革命结合起来,同时再跟政府部门去回应这些变化可能带来的走向结合起来,我想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个政府的类型。我参与了中国电子政府方案的讨论和起草,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从全球范围内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政府的类型大概有这么几类,一种类型我们把它称之为福利型政府,这种政府的典型是北欧或者说撒切尔以前的英国,什么东西都是政府管着的,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所有东西都是管着的。这种情况我想在日本也有所体现。第二种类型的政府我们把它称之为监管型政府,也就是说该管的管住,不该管的坚决不管,第二种类型非常典型的就是撒切尔以后的英国、美国政府或者英联邦国家。第三种类型的政府我们把它称之为发展型政府,非常典型的或者说很不幸的就是日本,日本严格意义上它是一个发展型政府,包括东亚。发展型政府在80年代后期以后或者说到90年代以后基本上有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这种大的变化在青木教授看来在日本被称之为“迷失的十年”或者被称之为“丢掉的十年”,同样在东亚的其他国家,这些发展型政府把所有的它们认为政府应该管,或者认为政府应该足够强大,或者认为应该与市场之间形成一个比较亲善的关系,所以事实它们把不该管的全部拉到了自己的怀里。还有一类政府,比如说像拉美的政府,我们把它称之为依附型的政府,它把一系列社会的、经济的想法靠在国际体系上,或者靠在可能出现的一些循环上,所以依附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有非常大的投机性。我们始终可以发现,拉美的经济不仅对国际经济进行投机,而且对本土有着非常大的赌博,押着非常大的赌注。例如在巴西,在其他拉美国家我们看到的是始终是一个市场均持的社会,比如说像汽车工业基本上存在着三三制的股权结构。还有一种是被俘虏型政府,比较典型的像非洲、中东,完全被利益集团俘虏。中国的情况我想可能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地域都有不同的政府的类型存在和体现。
IT革命正好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冲击机会,所以刚才荣教授提出来的、林教授又进一步阐发的制度的五个特性,我想非常重要。我在这里还要补充两点,一个是制度变迁的内生性取决于本土力量的变化,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什么样的东西是本土的,什么样的东西对制度来说通过移植或者说有意的模仿这种方式来产生一些所谓制度上的特性,我想这个可能很困难。刚才毅夫也讲了重化工产业或者说重工业化战略之所以失败,实际上是当时通过强制性的制度移植或模仿而导致的一个结果,这就是在内生性基础上要补充的一点就是要强调本土的资源,或者说本土制度变迁的特定要素。
第二个要补充的是,我最近在看施密特的“经济中的习俗”(Customs in Economy)一书,他指出,在制度的变化过程中如果践踏特定的社会规范或者说不尊重一些特定的社会规范,那么这种制度变迁的方向就会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步,你不知道从哪儿来,也不知道往哪儿去。我想对于下一步的政府能力来讲,或者说行政的透明度来讲,中国的政府也非常关注,一个就是SARS以后特别强调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问题,要通过信息的披露、规范的公开,来引导各级政府或者说整个政府的各个部门来对社会进行服务,来强化自己的公共管理。第二个是把模块化的一些设计或者说模块化的一些管理理念引进政府,传统意义上的看法从来都是认为公共物品无法按照市场来定价,但是模块化的东西引出现以后,引进政府也好,它给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起码可以把政府自身的行政成本降下来,我想一个没有自身执政或行政成本概念的政府,它所能够行使的政府能力是有限的。这一点,日本现在可能已经意识到了。我想这些就是我们从日本可以得到的启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