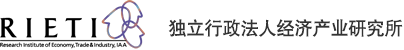亚洲的货币危机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处理过于苛刻,以及在对策和预测上的失误而扩大了。另一方面,在此后出现的货币危机中由于融资条件放宽,又产生了道德危机。人们期待IMF的作用向强化监督(监视功能)的方向发展。
发生问题的共同基础
从1997年到98年席卷东亚的经济危机是国际金融史上闻名的重大事件。正好在10年前的1997年7月2日,从泰国铢转为浮动汇率(Float)制开始发生的亚洲货币危机,在此后的6个月中扩展到包括韩国在内的亚洲所有地区。不仅给亚洲经济,也给政治体制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为什么从泰国向周边国家扩散的危机没能阻止住呢?即使已经过去了10年,在政策决策人员和学者之间也没能达成一致的看法。本文根据6月份出版的以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为核心编辑的《亚洲经济政策观察》特辑“亚洲货币危机十周年”的研究成果,重新探讨危机的原因,进一步思考危机带来的教训。
在危机之前,亚洲经济中已经存在着诱发货币危机的共同基础。这就是事实上的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Dollar peg)、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到期存款与货币的严重失调(双倍失调)、以及巨额短期资本的流入。
在泰国,经常项目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相比虽然高达8%,但流入的资本比赤字更多,因而外汇储备还在增加。一眼看上去经济好像非常健康。泰国的货币危机可以说是由于短期资本急速流出而导致的资本收支型危机。
另一方面,各国之间也存在不同的地方。泰国的货币危机源于外国的对冲基金和金融机构等投机家进行的货币投机,而与之相反,在其他国家中对冲基金的影响则非常有限。在印度尼西亚,本国居民的资本逃避比别的国家更多。而且在该国,由于IMF提出的融资条件(限制性条件),使货币危机发展成政治危机,导致了总统辞职。
诱因是流动性而非经济结构
另外,韩国货币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外国银行要求韩国银行归还贷款(拒绝延期),这也导致了财阀的重组。
无论是在泰国、印度尼西亚还是在韩国,IMF的实质融资总额都不足以遏止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在泰国的危机中,IMF和东亚国家进行了协调融资,虽然实现了超过IMF融资限度的融资,但即便如此也达不到恢复市场信心所需要的数量。
尤其是在宣布实施共计172亿美元的IMF和亚洲协调融资一揽子计划的同时,中央银行宣布自己所负担的未来美元抛售储备还有234亿美元,这也成为IMF计划无法恢复市场信心(泰铢的升值)的一个因素。在韩国和印度尼西亚,IMF以外的国家融资约定被置于“第二线准备”的位置上,市场看穿了这点钱只是拿来装饰门面,致使市场的信心未能得到恢复。实际上,第二线准备最终1美元也没有实现。
IMF虽然预先知道泰国很有可能发生货币危机,但泰国没有听从搞活外汇制度的建议,尝试货币防卫直到花光外汇储备为止,因而损失惨重。相反,在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直到货币危机变得严重起来之前,无论是IMF还是市场都没有意识到存在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可以说是由于泰国的货币危机没有被尽快遏止住而导致了危机的蔓延。
在印度尼西亚,11月IMF开出的关闭16家银行并削减存款的融资条件导致金融的不稳定进一步恶化。12月份当韩国陷入危机时,IMF改变了融资制度,将融资限度由此前实行的融资额的5倍调高到20倍。可以说IMF总算意识到了自己由于提供大规模流动性资金而具有的国际性“最终贷款人功能”(LLR)。但是,即使是这一金额也不足以抚平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安,最终于12月24日,G7和IMF说服向韩国提供贷款的银行(发达国家)维持融资余额,通过这种不合惯例的处置方式,危机总算向缓和的方向发展。
这是在民间追究借出方责任的新手法,结果大功告成。从韩国危机发生的状况(危机前宏观经济良好)、处理危机的方式(要求维持融资余额)、以及危机后经济的急速恢复来看,危机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经济结构上存在本质的问题,而可以说是由于借出方同时陷入恐慌,要求收回融资而导致的“流动性的危机”。
危机过后,除印度尼西亚以外,亚洲各国的经济都在1999年到2000年迅速恢复,在此之后也一直顺利增长。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资本收支型的货币危机则一直在持续。1998-99年巴西、2001年土耳其、2001-02年阿根廷遭受到货币危机。
在这些危机中,与亚洲货币危机相比,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可以发现IMF改变了方针。也就是说,与以往一直鼓励亚洲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制相反,为这些国家守住固定汇率制度(在土耳其是小幅度汇率调整)而第一次进行了融资。
显露出组织矛盾的结果
尽管坚持固定汇率制度从根本上看是不可能的,但由于没有附加上“先把货币贬值”这一苛刻的改革条件,很多政策决策人员和经济学家都感觉到意外。IMF解释说,当时鉴于亚洲货币危机的经验,考虑到货币的急速贬值容易导致接受融资国家的银行危机,而且如果不尊重接受融资国家的意向则约定的条件也不会得到遵守,所以容忍了固定汇率制度。
但是果如所料,这些国家在几个月后取消了IMF的计划,不得不贬值。最初IMF计划的融资,不过是给投资者从该国逃出的时间而已。与对亚洲各国的严格的约定条件相比,对亚洲之后的其他国家的处理看上去确实非常宽松。可以说IMF在亚洲货币危机中学习到的“教训”其实是错误的。
向基本上没有财政赤字、保持健全宏观经济的泰国之外的亚洲国家要求严格的融资条件,而在基本的宏观问题堆积如山的后亚洲货币危机中放宽融资条件,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给借出方与债务国双方都带来了道德危机。在思考国际货币体制时,为什么IMF在后亚洲的货币危机中将条件放宽到引起道德危机的程度,需要对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学进行思考。
在亚洲货币危机过去10年之后,东亚经历了危机的国家再次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经济改革进一步得到推进,与危机之前相比经济结构、特别是金融部门的体质得到了强化。在危机的翌年以后,经常项目收支保持了赢余,按照迄今为止使用的标准,外汇储备已经达到过于充足的水平。从不想再依靠IMF帮助的意识出发,各国正在加紧积累外汇储备。确实,今后亚洲陷入因为外汇储备不足而导致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很小。
进而言之,除土耳其之外,受到亚洲危机及之后的货币危机侵袭的国家基本上都已经基本还清了IMF的贷款,IMF已经无法取得足够填补支出的收入(通过对外贷款所得到的利息)。
虽然没有货币危机的世界应该不需要IMF,但为了消灭货币危机可以说IMF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如果危机可以防患于未然,那么IMF就会失去收入。由此也显示出了IMF的这一组织上的矛盾。
今后的IMF的存在意义应该在于成为一个监督者,从地区性和世界性方面对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观察,使其在中期范围得以维持。
2007年7月11日《日本经济新闻》